声音|罗日新:写出家乡所有的可敬可爱,写出自己所有的激情
发布时间:2025-11-07 返回
2025年11月3日,最新一期《人民文学》杂志刊登黄石籍作家罗日新的中篇小说《巴图姆往事》。这是继2022年长篇小说《钢的城》出版后,罗日新又一部扎根生活、书写黄石的文学力作走向全国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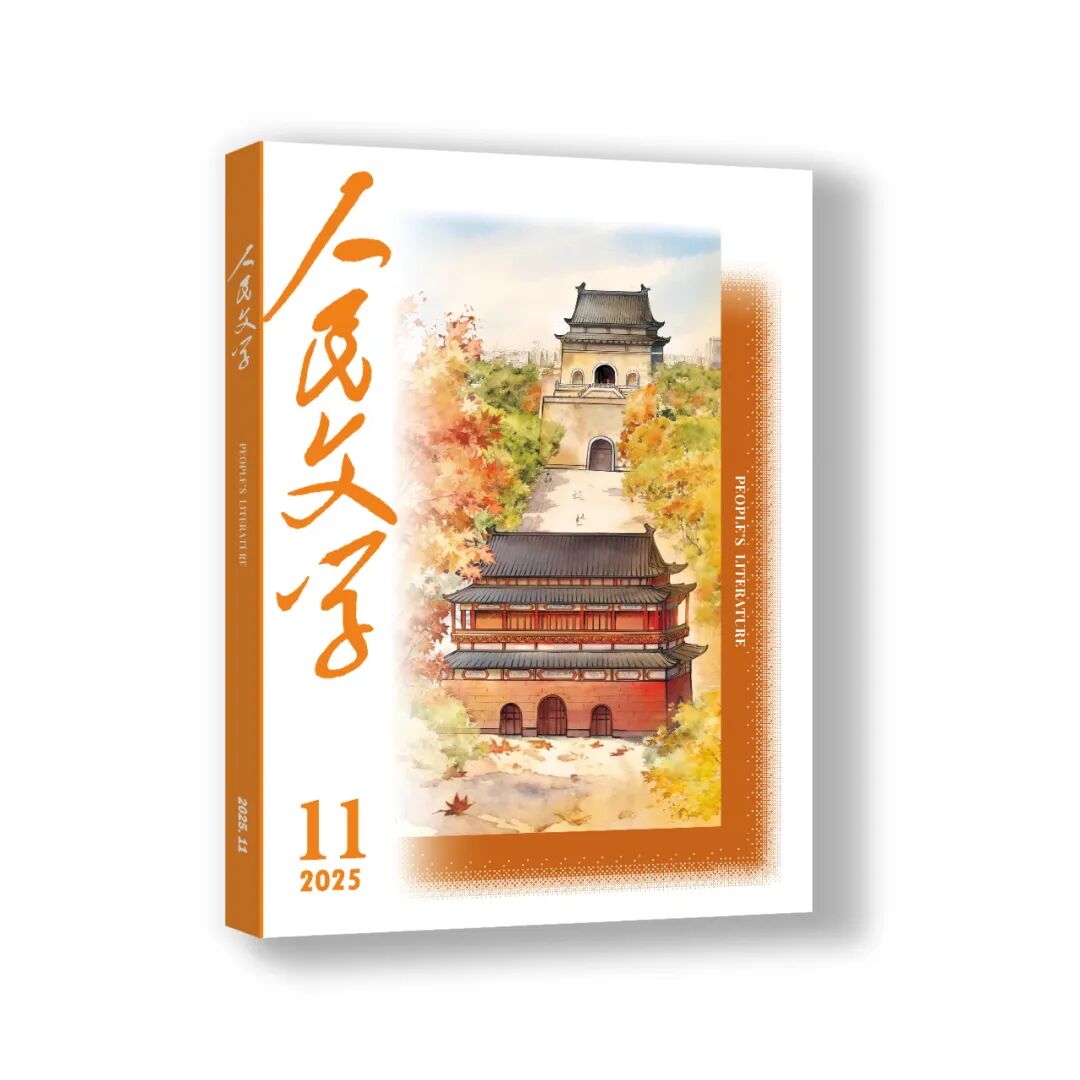
小说缘于真实事件
“我要通过他的眼睛和脚步,去践行一个朴素的信念”
《巴图姆往事》共3.1万字,以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,讲述黄石籍经侦老罗化身推销员,深入荒漠深处的中亚H国巴图姆石油小镇,追捕诈骗犯,为家乡的企业讨回公道的故事。巴图姆汇聚三教九流,环境嘈杂险恶,人情错综复杂,老罗与各种势力斗智斗勇,拨笋抽茧般理清涉案人的背景关系,最终将案犯诱捕回国。小说节奏紧凑、逻辑严密、语言简洁、人物形象鲜活,情节兼具悬疑小说的紧张感和现实主义文学的扎实性。

“在钢材和石油行业泡了这么多年,我知道太多关于国际贸易、商战骗局、人性贪婪和人间情义的故事。中国文学一直缺乏商业书写,商场如战场,这个领域是人性对决最激烈的地方。”接受黄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采访时,罗日新又谈文学,又谈经历。他介绍,2006年前后,国内钢材价格暴涨,不少企业急于在海外寻找矿山资源,这就给了一些不法分子可乘之机。他一个朋友就曾遭遇过跨国诈骗,虽然最终追回部分损失,但过程艰难曲折。
“这个真实案例的尖锐深深刺痛了我。商人也是普通人,也会轻信,也会犯错误,当然也有道义良知。所以,当他们面对贪婪与欺骗的时候,也有一筹莫展的时刻。但在法律的帮助下,在家乡人的情义加持下,更容易找到解决问题的出口。所以,商战故事也是故乡故事,也是情义故事。”罗日新很健谈,他说这个故事如种子一般在他心里长了很多年,“我意识到,我必须写下它。但思来想去,非虚构不如虚构更有宽度,更有力量,更能产生深刻的真实。于是,我找到了老罗这个角色,让他作为临江市经侦支队的支队长参与其中。而且在商人罗和警察罗之间,我巧妙利用读者容易对号入座的心理,设置了悬念,产生了一定的幽默效果。我其实想表达这样一个朴素的信念:无论你是谁,无论你逃到哪里,只要你在中国的土地上欺骗了中国人,就必定有人跨越千山万水,将你绳之以法。而生活再难,我们遇到再糟糕的事情,也不妨稍稍幽它一默。”
历时近三年艺术打磨
“写作的过程,是一个不断自我怀疑与扬弃的过程”
“《巴图姆往事》能够在《人民文学》2025年第11期上和诸位名家文友的大作一起散发油墨香,我非常激动。这一刻,距离2023年元月那个寒冷的下午我写下第一个字,已过去了两年又十个月。”在谈到小说的创作历程时,罗日新说道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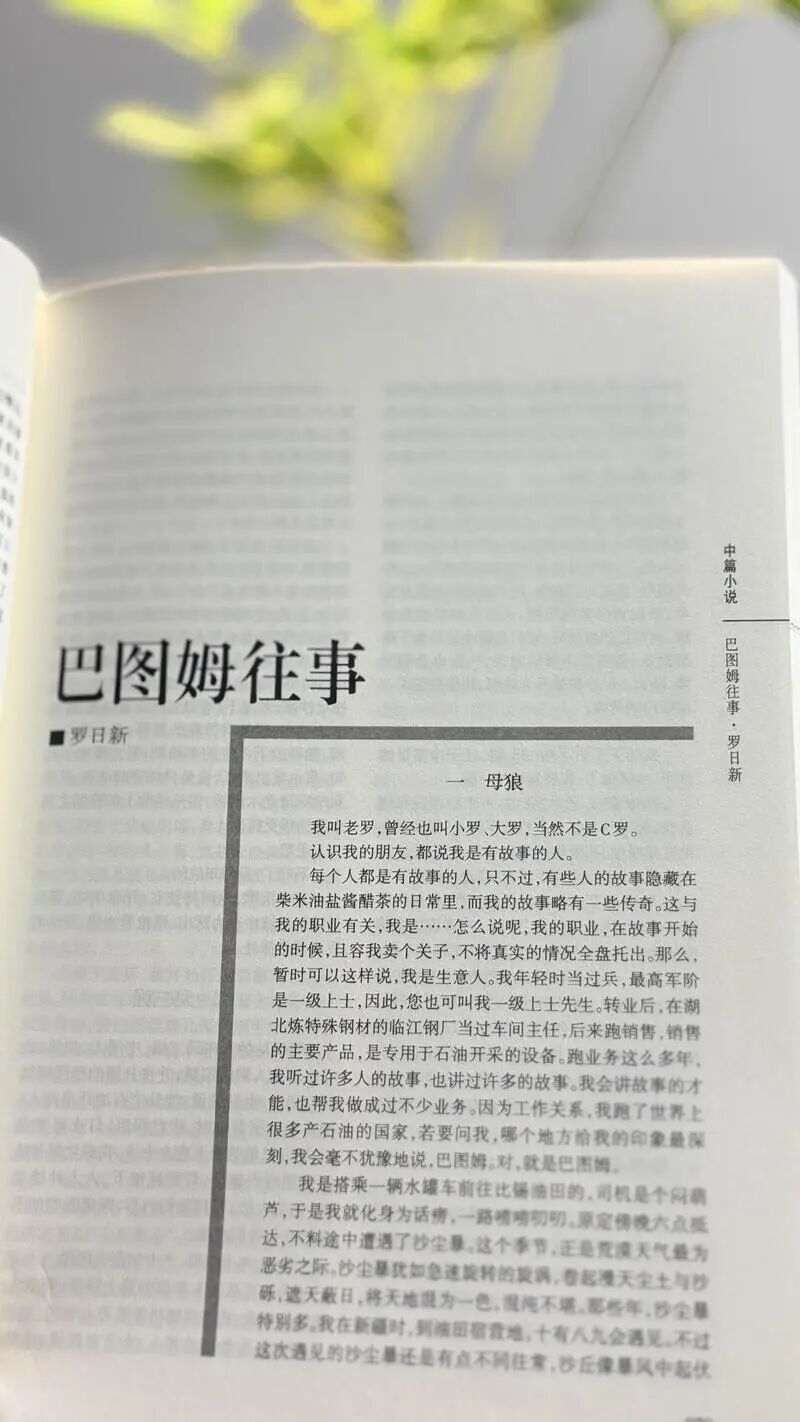
他表示,从《钢的城》的53万字到《巴图姆往事》的3.1万字,看上去体量小了,但难度丝毫不减,艰苦也不会削减分毫。当然,世间所有的事都是如此,不历苦痛难得甜蜜。而写作的过程,也是一个不断自我肯定又自我怀疑、不断吸纳又扬弃的过程。
“第一稿名字叫《中国公民》,有6万余字,我近乎执拗地完整复现了马三强的行骗链条。我试图用巨细靡遗的笔触,构建一个因果分明的世界。写完放了几个月后重读,我发现了问题:对中篇小说来说,某部分过于臃肿一定会冲淡故事核心的紧张感。于是,第二稿变成了4万字,名字也改成了《叫巴图姆镇的地方》。我开始尝试加入叙述技巧,打碎完整链条,让人物对话和心理活动也变成情节推进的方式。一个带有推理悬疑色彩的故事,读者需要的是即将引爆炸药的引信燃烧过程,而不是一份详细的炸药成分分析报告。”罗日新介绍,到第三稿时,他再次举起删改的利斧,再次聚焦最核心的矛盾,小说的标题也沉淀为更具故事感与回忆感的《巴图姆往事》,当然,因为巴图姆之于读者的陌生感,这个标题显得朴素却不普通。
“每一次修改,都不只是字数增减、题目变化那么简单,它更像是一场漫长而孤独的淬火,一遍遍将粗砺的矿石投入生活和艺术的熔炉,锤去杂质,最后用最妥帖的语言让故事露出自己想象极限的光泽。”罗日新说,“实在改不下去的时候,我就大声读,逐字逐句读给自己听。如今,所有那些自我压迫的日日夜夜,都化作了‘心有余悸的惊喜’。心有余悸,是深知创作之路艰险,惊喜,是庆幸自己最终没有辜负这个好故事的原石。”
工业城市的文学回响
从工业史诗到法网正义,不变的是对故乡的深情
罗日新的文学之路颇具传奇色彩。他青年时期曾有作家梦,却被父亲喝止。大学毕业后他成了大冶钢厂的技术员,从值班主任做到市场调研部长、钢管公司副总经理。1999年,35岁的他辞职下海,投身国际贸易。45岁开始尝试写小说,从此一发不可收拾。尤其是长篇小说《钢的城》的出版和广受好评,更是给了他莫大的鼓舞。

“作家梦被我爸打断之后,我就踏踏实实在钢厂工作,那时候最大的梦想是当厂长;下海经商后,我天天想的是如何把生意做大,做到全世界。”罗日新笑着说,“跟当厂长和做生意相比,写作更难,因为文无第一,所以,开始写作之后,我的梦想就变成了写出更好的作品,让自己每天进步一点点,每部作品进步一点点。”
目前为止,他两部重要的作品,背景城市都是“临江市”,也就是家乡黄石,这个他寄托了最深感情的地方。他说:“沈从文说过,一个战士,要么战死沙场,要么回到故乡。我觉得我的商业征战已经结束了,所幸没有粉身碎骨,还取得了那么一点点的成就,那么,接下来将陪伴我余生的写作,就要回到家乡、回到黄石。这里的江河湖山、工厂街道、市井人情,都是我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,也是我的艺术之根。”罗日新说。
如今,罗日新已经成为新大众文艺的代表,他诚挚的书写,换来的是读者诚挚的回应。有网友留言:“罗日新的作品让黄石这座城市有了文学的表达。《钢的城》写的是黄石的工业历史,《巴图姆往事》则展现了黄石人的精神气质。这种扎根故乡、面向世界的创作姿态,让人赞叹。”
的确,《巴图姆往事》的主要情节虽然发生在中亚荒漠,但“临江市”作为主人公“老罗”的故乡和精神依托,始终贯穿全文。小说第七章“背调”中,通过工头老贵的回忆,还有对临江市的生动描绘:“五十年代的苏式老房子、钢厂工人村、街口下棋的老工人……”这些细节都是黄石工业文化的真实写照,罗日新写的时候显然也用情至深。
罗日新说:“我父亲就是钢厂的老职工,我在工厂生活区长大。那些苏式老房子、街坊邻居围坐聊天的场景,都是我童年最深刻的记忆。”此外,小说主人公老罗的性格也是黄石性格的代表,长江码头文化中“不达目的不罢休”的执着、工业城市培养出的务实、工人阶级的集体主义,都在老罗身上得到体现。而且,他的追逃,不仅要维护法律的尊严,更要守护临江风清气正的经营环境和“工人村”平静和谐的生活。正是这种种精神的汇聚,支撑他在异国他乡克服重重困难,最终完成使命。
“黄石基因在我的精神血脉里,长江性格会永远在我的故事里流淌。我会一部部写下去,写出家乡所有的可敬可爱,写出自己所有的激情。”罗日新说。是的,火热的时代、沸腾的生活、宽广博大的家乡,永无止境的艺术探求,哪一个都在召唤写作者,越过高原,攀上高峰。